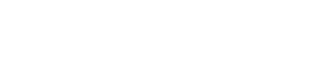6月29日早上九點(diǎn)半,梭子丘村十天一次的市集已然人頭攢動。文新學(xué)院“文梭新韻”實(shí)踐團(tuán)成員在水果攤前停下腳步,一顆本地李子入口,甜味稀薄,果肉微澀。
“我們這兒水土不養(yǎng)甜果。”攤主谷阿姨坦言,攤上脆甜的桃子、李子大多從四川遠(yuǎn)道而來。梭子丘的土地似乎更偏愛煙草、玉米這類經(jīng)濟(jì)作物,水果的甜蜜成了需要“進(jìn)口”的奢侈品。“十年前趕集,賣的是自家種的土豆、玉米,現(xiàn)在攤位上多了四川李子、貴州辣椒。”谷阿姨一邊給顧客稱重,一邊用流利的普通話說著。作為梭子丘村白族聚居區(qū)的居民,她見證了這場蛻變:曾經(jīng)靠天吃飯的村民,如今通過種植煙草、玉米等經(jīng)濟(jì)作物,借集市平臺將農(nóng)產(chǎn)品銷往周邊鄉(xiāng)鎮(zhèn),年租金收入超四千元的攤位,成為脫貧成果最鮮活的注腳。
穿過短短五百米的街巷,二十四家攤位擠擠挨挨,空氣里蒸騰著米酒的醇香、公婆餅的焦脆。金黃酥脆的公婆餅是當(dāng)?shù)匾唤^,綴滿白芝麻與翠綠蔥花的表皮,咬開便是土家族特有的煙熏臘肉與山胡椒交融的濃香。不遠(yuǎn)處,卓阿姨的雙手在案板上翻飛,薄皮裹著肉餡,指尖一捏便誕生一只精巧的餛飩,日復(fù)一日的勞作化為令人驚嘆的熟稔。
這場趕集不僅是一場鄉(xiāng)土物產(chǎn)的展銷,更成為觀察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窗口。支付方式的變遷尤為典型,在集市入口處,賣苞谷酒的高師傅正忙著給酒壇貼上收款碼。“年輕人用抖音查趕集日,老人也學(xué)用微信掃碼。”他笑著說。官方數(shù)據(jù)顯示,盡管現(xiàn)金交易仍占主流,但60歲以上的攤主中已有近兩成嘗試數(shù)字支付,普通話普及率突破80%。這些細(xì)節(jié)折射出語言扶貧與鄉(xiāng)村振興在深山中的扎根。
走訪中,成員們敏銳捕捉到一絲失落:白族風(fēng)情在市集的煙火氣中幾近隱形。攤主們身著便裝,交流時(shí)操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無疑是推普深入人心的明證,但正如谷阿姨所言:“我們祖上是白族,可如今老的東西,不太顯了。”那承載著民族記憶的精巧繡片與獨(dú)特衣衫,在今日的市集中竟難覓蹤跡。
在實(shí)踐團(tuán)看來,梭子丘村的集市如同一面多棱鏡,映照出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瓶頸、數(shù)字鴻溝等問題的同時(shí)也清晰描繪著脫貧攻堅(jiān)與推普工作的顯著成效。那亟待擦亮的白族文化明珠,無疑是未來文旅融合、深化振興最具潛力的方向。當(dāng)特色農(nóng)產(chǎn)與深藏的民族風(fēng)情真正交織在一起,這片土地所孕育的特色文化,才能超越時(shí)空的限制,成為吸引遠(yuǎn)方目光、滋養(yǎng)一方水土的真正寶藏。
(文/劉鑌方、戰(zhàn)彥回、楊樹濤 圖/羅令馳 一審/周云鵬 二審/劉莎 三審/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