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日�,世界著名出版公司Elsevier發布2014年中國高被引學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單,將1651名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學者(覆蓋經濟��、人文��、醫學、能源�、計算機等近40個學科領域)呈現在學術界和公眾面前��,我校蔣仁言教授入選該榜單的“安全,風險�����,可靠性和質量”學科領域�����。
“我喜歡自己在做的事”
記者:蔣教授���,您是如何看待這次入選的�����?
蔣仁言:這次能入選,確實很不容易��。一方面��,我的入選主要依據我回國后最近這九年所發表的論文,而文章發表得越早被引用的機會越大�;另一方面���,我是獨立研究���,沒有別人團隊作戰那么有優勢���。此次入選令我感到自豪�,因為它以客觀數據讓評價變得有據可依,更具說服力��。
另一件令我感到自豪的事是國際雜志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可靠性工程與系統安全》)邀請我當編委���。該雜志本屆編委會中總共有46名編委����,中國大陸就我一個���。這是我巨大的榮譽����,因為編委名單一公布就反映了這些人在領域內的學術地位。
記者:據了解,您發表了140余篇學術論文���,獲湖南省自然科學一等優秀學術論文3次,還出版了5本專著,您在科研方面有哪些經驗、心得�?
蔣仁言:真正做研究的人是享受研究過程的���,興趣是第一位的��。那么,興趣是如何產生的呢?我認為是通過不斷的學習轉變為個人追求,通過培養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來發現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八九十年代�,長沙交通學院很多老師下海,但我堅持到現在��,因為我喜歡自己在做的事��。
在當前浮躁的社會中����,有時�����,過分的激勵會導致人們功利化的追求、功利化的學術。在名利的刺激下����,有人愿意冒風險�,從而產生學術不端�����。真正做學問的人�,為的不是獎項�����、金錢���,而是享受研究過程本身����。當然��,學問做得好����,成為資深行家���,可能會有名有利�����,但即使沒名沒利還是得干,因為這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治學靠的是興趣,興趣可以引領追求����,不用別人強迫�����。
記者:目前學校處于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學校將對科研與教學體制進行改革�����,為青年教師創造有利條件�����,搭建發展平臺���,鼓勵青年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您對青年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有些什么建議����?
蔣仁言:我覺得��,首先要有扎實的基礎���。其次����,不要急功近利�����,科學研究不會立竿見影��。再次,要理論聯系實際���。毛主席說過,“要深入生活�,要深入實際”����,科學研究也是這樣�。比如行業、企業面臨的問題是什么�,這需要通過交流來了解實際情況和國際動態����。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問題���,通過研究解決問題��,產生有實際價值的理論成果。如果僅僅在家拍腦袋�,是出不了有價值的東西���。藝術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學術也是如此��。
“要有崇高的科學精神和良好的科學素養”
記者:近年來,一些高校老師剽竊、抄襲他人科研成果的學術不端行為屢被曝光。您對學術不端是怎么看的�?如何才能杜絕學術不端行為���?
蔣仁言:學術不端行為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不能僅靠計算機軟件的鑒定來說明問題。有些行為屬于灰色地帶,由于出現在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沒有被關注����,被發現。例如,當一篇論文中用到“本文第一次……”這樣的表述時����,就要求作者對論文所涉領域的國際前沿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否則���,就可能進入“灰色地帶”�。因此��,近年來曝光的學術不端行為只是冰山一角�����,但足以反映整個學術生態的惡化���。
我認為�,要杜絕學術不端行為,一是要有崇高的科學精神����,二是要有良好的科學素養���。比如我們畫大小兩個同心圓��,小圓是道德的邊界��,大圓是法律的邊界。跨過道德的邊界后雖然沒有觸碰到法律的邊界�����,卻已經違背了道德���,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高尚的科學精神��、良好的科學素養來自律�����、自省。
記者:有人說,學術自由是大學的靈魂,唯有充分享有學術自主權,富有濃厚的學術氛圍的大學,才能真正找回大學的“自我”��,大學也才能正確地享受其他的權利�,主動、自覺地走向社會中心����。請您談談對學術自由的看法。
蔣仁言:這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我所知�,沒人會干涉你的研究方向�����,也沒人要求你研究什么����,學術研究應該說是自由的���。與其說學術自由是一個問題�����,還不如說學術資源的分配是一個問題���。
“科研‘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記者:您目前正在進行哪方面的學術研究����?進展如何?
蔣仁言:目前仍在進行質量��、可靠性與維修的研究�。“安全��,風險����,可靠性和質量”領域是一個很前沿的領域,這對所有的工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都是有需要的���。國際上對于這個領域已經非常重視,在我國卻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科研進展用一句話說就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有科學家說過�����,“知道的越多��,就越是發現自己未知的東西越多”����??茖W研究只會增速,不會減速。假定知識增長率與現有掌握的知識成正比,則知識呈指數增長����。由于“未知的東西多”�����,“知識增長快”�,一個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在一個領域是會持續不斷的研究下去的���。因為現有方法或技術總是在持續改進之中��,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不斷發展的�����。
記者:您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面頗有成果����,而且在教學上推陳出新����,推出了“質量與可靠性工程”雙語教學示范課程,并潛心編寫適合本校學生具體情況的教材。您平時是怎么把科研成果滲透到教學中去的���?
蔣仁言:在我看來,科研和教學不是分離的,它們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直接��、定量評價教學質量很難��,而教師學術水平相對來說更易定量評價。因此,國際上通常認為教師的學術水平與教學質量是高度相關的,直接評價教學質量�����,不如評價教師的學術水平����。優秀的教師不能等別人更新教材后再照搬到講臺,而應該主動掌握所在學科的最新知識。單憑教師的課堂表現(如儀態��、ppt���、備課情況����、進程等)是無法判斷所講授的內容是否先進、恰當��。只有“內行”才能看出“門道”來�。所以我們更應該關注教師自身的知識水平�。
記者:您覺得一所學校理想的師資隊伍應該是怎么樣的?
蔣仁言:我曾請教過我的導師什么是國際一流大學����,他說國際一流大學“70%以上的教師是站在所在領域的國際前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一所大學的教師大致可分為五個層級(每個層級還可再分)�����。初級幾乎不做研究����;二級圍繞某個題目(Topic)做點研究����,研究范圍比較窄��;三級研究幾個相互關聯的課題(Topics);四級對某個學科領域都懂(Subject)���;五級就是大師,學貫中西�����,能夠在相互關聯的幾個學科領域做研究(Subjects)��。
如果用橫座標代表等級�����,縱座標代表各等級的教師比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師資質量分布圖。在我國�,好的學校的師資等級的平均值可能在二�、三級之間�����;差一點的學校的等級平均值可能在一���、二級之間�����;很少擁有三、四�、五級的教師��。名校和非名校的差別可能就在這里。
【人物名片】
蔣仁言教授�����,1956年生���,長沙理工大學汽車與機械工程學院“質量���、可靠性與維修研究所”所長���,國際雜志“Reliability Engineeering & System Saf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liability & 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rformability Engineering”編委����,中國運籌學會可靠性分會理事�,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可靠性分會委員會委員,中國設備工程專家庫高級專家,全國汽車行業設備管理理事會顧問���;1996年獲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博士學位;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學、加拿大Saskatchewan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澳大利亞昆士蘭工業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或合作研究�;發表各類學術論文140余篇��,其中��,國際雜志論文65篇,國際會議論文55篇,并大量被SCI、EI收錄;出版專著5本,其中兩本專著《Introduction to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Engineering》和《Maintenance: Decision Models for Management》獲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基金資助出版;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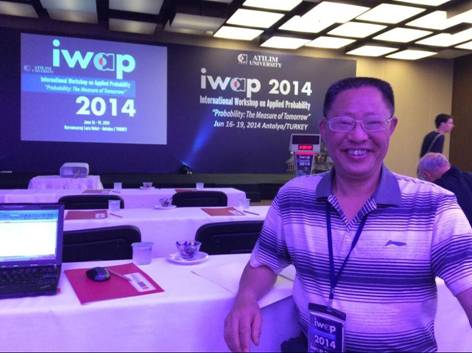
附件:
上一篇:中教評論:遏制學術不端需獨立第三方鑒定
下一篇:2014年中國科技界反腐案件大盤點